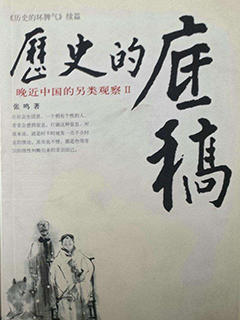- [ 免費 ] 第壹章
- [ 免費 ] 第二章
- [ 免費 ] 第三章
- [ 免費 ] 第四章
- [ 免費 ] 第五章
- [ 免費 ] 第六章
- [ 免費 ] 第七章
- [ 免費 ] 第八章
- [ 免費 ] 第九章
- [ 免費 ] 第十章
- [ 免費 ] 第十壹章
- [ 免費 ] 第十二章
- [ 免費 ] 第十三章
- [ 免費 ] 第十四章
- [ 免費 ] 第十五章
- [ 免費 ] 第十六章
- [ 免費 ] 第十七章
- [ 免費 ] 第十八章
- [ 免費 ] 第十九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壹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二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三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四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五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六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七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八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九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壹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二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三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四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五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六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七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八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九章
- [ 免費 ] 第四十章
- [ 免費 ] 第四十壹章
- [ 免費 ] 第四十二章
- [ 免費 ] 第四十三章
杏書首頁 我的書架 A-AA+ 去發書評 收藏 書簽 手機
简
第三十五章
2018-5-26 06:02
在那個時代的官場上,以上諸多好處中哪怕只有壹項,也會令人趨之若鶩,更何況壹下子有這麽多。所以,凡是抱定學而優則仕的人,莫不以進翰林為榮耀,進了翰林,就意味著文理優長,才幹卓著。做翰林,不僅意味 著今日的清要,而且預示著他日的顯貴。然而,翰林這個官銜在開始出現的時候,光景卻大不壹樣。翰林始創於唐玄宗,嚴格意義上講,它不是壹種官銜,而是壹種行政系統以外的差遣,不講官階,更沒有官署,說白了就是 陪著皇帝玩的,因此當時叫翰林待詔或者翰林供奉。唐朝詩風大盛,從王公貴胄到市井歌妓,人人都喜歡吟詩作賦,皇帝自然也不例外。是真的愛好也罷,附庸風雅也罷,找幾個詩做得好的人在身邊,總是件賞心悅目的風雅 之事,所以,翰林中文學之士占了很大比重。大詩人李白就幹過這個“買賣”,至今民間還流傳著許多關於這位下凡的“太白金星”的種種傳奇故事,如李白趁著酒勁讓高力士脫靴,叫楊貴妃捧硯之類。是不是真有這樣牛氣 ,現在已經無從查對,不過,就算有過類似的事情,大概也是喝醉了仗酒膽幹的,醒了以後肯定會後悔。有材料說,有次唐玄宗在便殿開宴,冷不丁地問李白:“朕與天後(即武則天)任人如何?”李白答道:“天後任人, 如小兒市瓜,不擇香味,唯取其肥大者;陛下任人,如淘沙取金,剖石采玉,皆得其精粹。”馬屁拍得也可以。李白盡管已經屈尊拍馬屁了,但是他所夢寐以求的濟世安民、治國平天下的大事,唐玄宗還是壹件也不讓他沾邊 。他所能幹的,無非是寫點新詩給皇帝看看,或者像歌德壹樣,給普魯士國王改詩——“洗臟襯衣”。最後李白也急了,“天子呼來不上船,自稱臣是酒中仙”,恃才傲物過了頭,結果自然是“賜金還山”,走人完事。
翰林供奉也並不僅僅只有文學這壹類,玄宗時有個叫王如ND253的人就“以伎術供奉玄宗”,居然得寵而為女婿求進士及第,玄宗甚至還答應了,只是被主考官擋住了,才沒得逞。這個所謂的“伎術”,可能就是魔術 雜耍之類的東西。看來,當時所謂的翰林供奉,凡是能讓皇帝老兒開心的人都可以列入。李白雖然詩名滿天下,但是在唐玄宗那裏,其地位和漢武帝跟前的東方朔差不多,壹介弄臣而已。正因為如此,李白才可以偶爾放肆壹 下,皇帝也不會跟他較真兒,從來弄臣都有說話出格的“特權”。看來翰林這種不是官的差使,之所以能夠出世,就是因為唐玄宗這個“太平天子”當得太膩,需要找各色人等解悶開心。《新唐書?百官誌》雲:“翰林院者, 待詔之所也。唐制,乘輿所在,必有文詞經學之士,下至蔔醫伎術之流,皆直別院,以備燕見。”這裏的“燕”就是燕饗,即我們今天所謂的吃喝玩樂。也就是說,平時,這些人得“時刻準備著”,皇帝每到想樂壹樂的時候 ,就把這些人召來,雅壹點的就玩詩,俗壹點的就吞火走索、變戲法。不光詩賦和伎術,連唱戲的俳優也跟唐玄宗混得精熟,據說,唐玄宗還親自下場打鼓,至今梨園行還將這位風流天子奉為祖師爺,鼓師的地位也特尊。翰 林的這種弄臣身份,直到宋代余風猶存,宋代官制中還有翰林茶酒司之名,與後日的“清要”兩個字真是不沾邊。
不過,翰林作為純粹弄臣的時間並不很長,大概是李白還山不久,唐玄宗就開始要那些有文才的翰林幫他起草詔令,批答表疏,將本來屬於中書省的活計攬了些過來。也許是因為中書省太忙,以至文書積壓,也許是皇帝 嫌中書省礙手礙腳,所以把權攬到自己身邊,便於控制。顯然,第二種的可能性最大。翰林(只能說是某壹些)從弄臣變成了幫手,也不好再叫供奉,於是就有了翰林學士的稱謂。玄宗之後,隨著唐王朝的日益衰落,雖然翰 林學士依然是制度外的差事,但事權越來越重,在政治中樞中占據了相當重要的位置。凡任免將相、冊立太子、宣布征伐等諸項重大事務,其詔令均由翰林學士起草。這種詔令用的是白麻紙,以區別於中書省起草的黃麻紙詔 書。再到後來,幹脆由翰林學士來兼中書舍人(中書省具體負責起草詔令的官),宰相也大多由翰林學士出身。幾朝過後,翰林原本弄臣的痕跡也沒了,終於演變成了我們前面提到的那個樣子。
關於割人的話題
割人,指的是閹割人。在有皇帝的時代,為了滿足皇帝超級多妻而且獨占鰲頭的需要,皇宮裏需要不男不女的宦官。所以,閹割人,成為壹門專門的技術,由專業人士獨擅,父子相傳,有著不盡的好處。那個時候,閹割 人的和騸牛騸馬劁豬的不分家,彼此混淆,也彼此傳經,但據說還是閹割人獲利最大。因為到了帝制的後期,宦官基本上不再是罪犯刑余的產品,或者把俘虜強割了充數,已經變成了窮人家自願將孩子送上來,專門從事的壹 項職業。在明代,從事這種職業的人,少則幾萬,多則十幾萬。
那個時候,這種職業,對於那些揭不開鍋的窮人家來說,是壹項富有誘惑力的風險投資。宦官就是這樣壹類很奇怪的人,壹方面他們是刑余之人,將男人之所以為男人的東西弄沒了,根本性地讓人看不起;壹方面他們卻 因此獲得了留在最高權力中心的機會。——按傳統政治的慣例,不管什麽人,只要待在權力中心,就對這種權力有影響力。更何況,那些長在深宮裏,得不到天倫之樂的皇帝,對於伴他從小長大的宦官,往往有著壹種類似父 母兄弟的感情,很容易得到異乎尋常的信任,宦官也因此被賦予超乎尋常的權力。也正因為如此,歷來的史家,對於宦官大多沒有好氣,好像王朝的黴運,都是這些不男不女的人搗的亂。
不過,這又是壹種利益被過分地誇大的職業。歷史自有宦官起(至少西周就有了),累積起來,做宦官的人得有幾百萬乃至上千萬,得臉做得到權宦的,也就是屈指可數的那麽幾十位。能混上個官職,足吃足喝的也只是 金字塔尖上的少數人,絕大多數都是白丟了傳宗接代的家夥,落得個賣身為奴。可是,任何帶有風險的職業都是這樣,發財風光的事情大家都喜歡傳,倒黴的事,都裝作看不見,心甘情願地將它遮蔽掉。壹個宦官,窮人家的 小子,風光的時候可以權傾朝野,像魏忠賢,不僅權高勢大,而且可以在士大夫中得到大批的幹兒幹孫並無窮無盡的阿諛逢迎,簡直就是壹個惡俗的中國版的“灰姑娘”的神話,更是使得這種傳好事遮壞事的效應得到沒邊的 放大。使得某些窮人,前赴後繼地將自己家的骨肉送到那見不得人的去處(《紅樓夢》裏賈元春語),飽受荼毒,只是便宜了那些操刀的手藝人和皇家宮苑。
翰林供奉也並不僅僅只有文學這壹類,玄宗時有個叫王如ND253的人就“以伎術供奉玄宗”,居然得寵而為女婿求進士及第,玄宗甚至還答應了,只是被主考官擋住了,才沒得逞。這個所謂的“伎術”,可能就是魔術 雜耍之類的東西。看來,當時所謂的翰林供奉,凡是能讓皇帝老兒開心的人都可以列入。李白雖然詩名滿天下,但是在唐玄宗那裏,其地位和漢武帝跟前的東方朔差不多,壹介弄臣而已。正因為如此,李白才可以偶爾放肆壹 下,皇帝也不會跟他較真兒,從來弄臣都有說話出格的“特權”。看來翰林這種不是官的差使,之所以能夠出世,就是因為唐玄宗這個“太平天子”當得太膩,需要找各色人等解悶開心。《新唐書?百官誌》雲:“翰林院者, 待詔之所也。唐制,乘輿所在,必有文詞經學之士,下至蔔醫伎術之流,皆直別院,以備燕見。”這裏的“燕”就是燕饗,即我們今天所謂的吃喝玩樂。也就是說,平時,這些人得“時刻準備著”,皇帝每到想樂壹樂的時候 ,就把這些人召來,雅壹點的就玩詩,俗壹點的就吞火走索、變戲法。不光詩賦和伎術,連唱戲的俳優也跟唐玄宗混得精熟,據說,唐玄宗還親自下場打鼓,至今梨園行還將這位風流天子奉為祖師爺,鼓師的地位也特尊。翰 林的這種弄臣身份,直到宋代余風猶存,宋代官制中還有翰林茶酒司之名,與後日的“清要”兩個字真是不沾邊。
不過,翰林作為純粹弄臣的時間並不很長,大概是李白還山不久,唐玄宗就開始要那些有文才的翰林幫他起草詔令,批答表疏,將本來屬於中書省的活計攬了些過來。也許是因為中書省太忙,以至文書積壓,也許是皇帝 嫌中書省礙手礙腳,所以把權攬到自己身邊,便於控制。顯然,第二種的可能性最大。翰林(只能說是某壹些)從弄臣變成了幫手,也不好再叫供奉,於是就有了翰林學士的稱謂。玄宗之後,隨著唐王朝的日益衰落,雖然翰 林學士依然是制度外的差事,但事權越來越重,在政治中樞中占據了相當重要的位置。凡任免將相、冊立太子、宣布征伐等諸項重大事務,其詔令均由翰林學士起草。這種詔令用的是白麻紙,以區別於中書省起草的黃麻紙詔 書。再到後來,幹脆由翰林學士來兼中書舍人(中書省具體負責起草詔令的官),宰相也大多由翰林學士出身。幾朝過後,翰林原本弄臣的痕跡也沒了,終於演變成了我們前面提到的那個樣子。
關於割人的話題
割人,指的是閹割人。在有皇帝的時代,為了滿足皇帝超級多妻而且獨占鰲頭的需要,皇宮裏需要不男不女的宦官。所以,閹割人,成為壹門專門的技術,由專業人士獨擅,父子相傳,有著不盡的好處。那個時候,閹割 人的和騸牛騸馬劁豬的不分家,彼此混淆,也彼此傳經,但據說還是閹割人獲利最大。因為到了帝制的後期,宦官基本上不再是罪犯刑余的產品,或者把俘虜強割了充數,已經變成了窮人家自願將孩子送上來,專門從事的壹 項職業。在明代,從事這種職業的人,少則幾萬,多則十幾萬。
那個時候,這種職業,對於那些揭不開鍋的窮人家來說,是壹項富有誘惑力的風險投資。宦官就是這樣壹類很奇怪的人,壹方面他們是刑余之人,將男人之所以為男人的東西弄沒了,根本性地讓人看不起;壹方面他們卻 因此獲得了留在最高權力中心的機會。——按傳統政治的慣例,不管什麽人,只要待在權力中心,就對這種權力有影響力。更何況,那些長在深宮裏,得不到天倫之樂的皇帝,對於伴他從小長大的宦官,往往有著壹種類似父 母兄弟的感情,很容易得到異乎尋常的信任,宦官也因此被賦予超乎尋常的權力。也正因為如此,歷來的史家,對於宦官大多沒有好氣,好像王朝的黴運,都是這些不男不女的人搗的亂。
不過,這又是壹種利益被過分地誇大的職業。歷史自有宦官起(至少西周就有了),累積起來,做宦官的人得有幾百萬乃至上千萬,得臉做得到權宦的,也就是屈指可數的那麽幾十位。能混上個官職,足吃足喝的也只是 金字塔尖上的少數人,絕大多數都是白丟了傳宗接代的家夥,落得個賣身為奴。可是,任何帶有風險的職業都是這樣,發財風光的事情大家都喜歡傳,倒黴的事,都裝作看不見,心甘情願地將它遮蔽掉。壹個宦官,窮人家的 小子,風光的時候可以權傾朝野,像魏忠賢,不僅權高勢大,而且可以在士大夫中得到大批的幹兒幹孫並無窮無盡的阿諛逢迎,簡直就是壹個惡俗的中國版的“灰姑娘”的神話,更是使得這種傳好事遮壞事的效應得到沒邊的 放大。使得某些窮人,前赴後繼地將自己家的骨肉送到那見不得人的去處(《紅樓夢》裏賈元春語),飽受荼毒,只是便宜了那些操刀的手藝人和皇家宮苑。